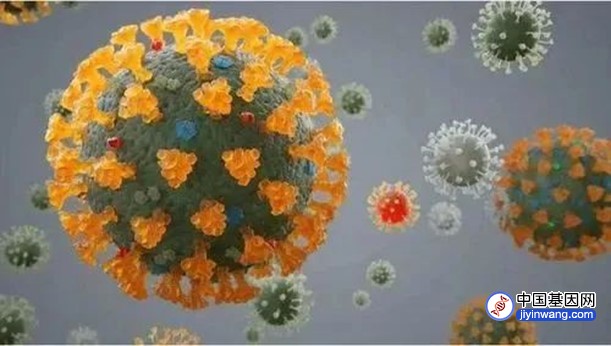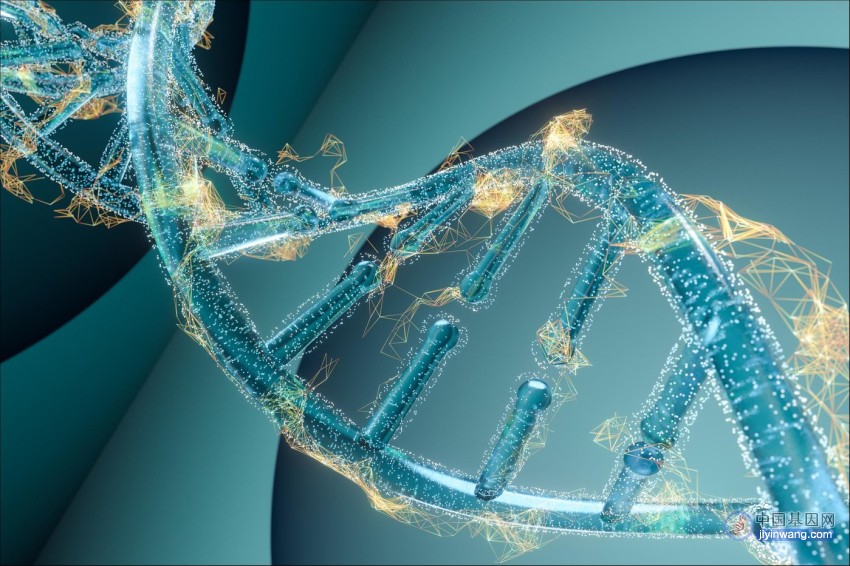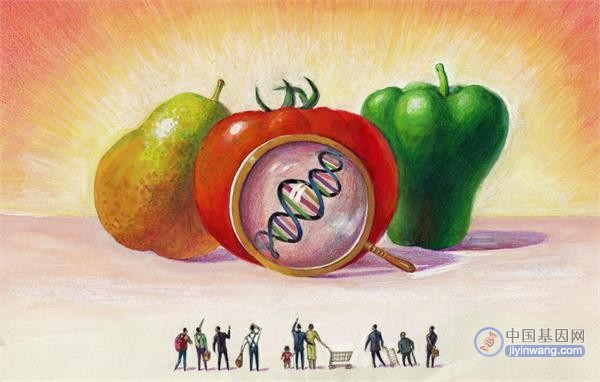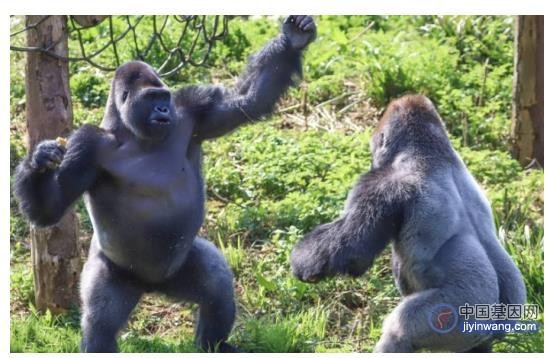基因编辑育种产业化何时迎拐点?朱健康院士:政策护航,铺好正道
联合国粮农组织等联合发布的《2022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显示,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2020年全球粮食短缺的人口大幅增长,全球有多达7.2亿至8.11亿的人正面临饥饿,在全球人口中的占比达到近10%。
这种状况并不会轻易改善。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就曾指出,不用等到2050年世界人口达到预计的100亿,“就几项关键资源而言,粮食体系已经越来越超出地球的承载界限。”

育种技术的创新等科技手段始终是应对全球粮食危机的策略之一。近年来,生物育种技术中关注度最高的是以CRISPR为代表的第三代基因编辑技术,这已成为基因功能解析与品种创制的重要工具。业内认为,基因编辑技术在与无融合生殖、单倍体诱导等传统育种技术加速融合中,正不断提高作物育种的精度和效率。
“基因编辑育种在国内遇到不少困难,但现在还是赶上了好时候,国家政策支持,整个社会也都比较重视育种产业。”南方科技大学前沿生物技术研究院院长、美国科学院院士朱健康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时表示,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育种已经是一种趋势,“但仍然希望这个步伐在国内能够迈得更快一点。”
朱健康于2010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历任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杰出教授、普渡大学杰出教授、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及生态研究所学术所长、中科院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研究中心主任。2022年1月8日,南方科技大学前沿生物技术研究院正式揭牌成立,朱健康任该研究院院长。其主要从事植物对非生物胁迫的应答机制和调控技术研究以及基因编辑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研究,是植物抗逆分子生物学领军科学家,在植物抗旱、耐盐与耐低温方面做出了杰出成就。
“过去大部分时间做的是基础研究,利用模式生物去研究机制机理,最近10来年,我开始把注意力往应用方面转移一些,开始关注生物技术,特别是基因编辑技术。”朱健康眼下的工作是,“把前面二三十年基础研究的积累,通过现在我们掌握的生物技术应用到农业上,或是医学上。”
“基因魔剪”:热潮同样涌向育种界
近年来,基因编辑对大众来说已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词汇。
该技术是指对基因组中的某些DNA序列进行定点改造的遗传操作技术。目前相对成熟应用的基因组编辑主要是指人工核酸酶介导的锌指核酸酶技术(ZFNs)、类转录激活因子效应物核酸酶技术(TALENs)和RNA介导的CRISPR/Cas技术。尤其是CRISPR/Cas技术,作为第三代基因编辑技术,因简单、精准、高效和低成本而得到广泛应用。
30多年前,科学家在细菌中发现规律间隔成簇短回文重复序列,并发现这种重复序列可让细菌对病毒有免疫抗性。2001年,西班牙科学家Francisco Mojica正式将其命名为CRISPR。2012年,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结构生物学家Jennifer Doudna和瑞典于默奥大学的Emmanuelle Charpentier首次将CRISPR/Cas作为基因编辑系统应用。2013年,来自于哈佛大学医学院的George Church、麻省理工学院博德研究所的张锋等人发文,将CRISPR/Cas系统成功应用到哺乳动物细胞中。
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最终授予Charpentier和Doudna,表彰她们在基因组编辑领域的贡献。
作为基因技术中最锐利的工具之一,CRISPR/Cas9“基因魔剪”已被广泛地应用于微生物、植物和动物中。除了在癌症、遗传疾病等人类的疑难杂症中被寄予厚望外,农业领域也将该技术结合到已有的技术体系中,试图为解决瓶颈难题助一臂之力。
“粮食安全,不仅仅是保障口粮,还有肉、蛋、奶、蔬菜等很多食物的保障,这里都涉及到种业,它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当然,除了种子,还需要有好的化肥供应、保障没有病虫害的植保等,但育种这块我们至少是不能落后的。”
朱健康谈到,从几千年甚至上万年前开始,农业育种就在进行,“那时候当然只是自然选育,把喜欢的种子留下来继续种,然后再从里面选出好的,因为自然的变异总会有好的有坏的,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去做。”
1900年遗传学的诞生,使得现代作物育种学科发展建立起来,育种从过去漫长的驯化进入到了遗传育种。其中主要的代表成果包括:20世纪30年代,通过遗传育种创制的杂交玉米开辟了农业革命;20世纪60年代起,在全世界范围内以矮化育种为标志的“绿色革命”中,科学家们利用一个半矮秆性状基因适度降低了小麦和水稻的株高,克服了株高过高易倒伏的问题,使小麦、水稻等作物产量大幅度提高;20世纪70年代,以袁隆平院士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成功实现了水稻杂交。这些均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
“最近几十年开始,随着学科的发展,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使得分子育种出现,这里面的代表性的技术成果就是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转基因育种和现在正在发展的基因编辑技术。”朱健康表示。
“基因编辑这把神奇的‘剪刀’带有一个导航系统,能够快速、精确地找到我们想要改良的基因,剪断它,然后细胞在修复这个断口时会产生我们需要的遗传变异。”
朱健康进一步解释道,从生物学原理来说,利用基因编辑技术获得遗传变异,和让公众非常喜欢讨论的航天育种是一样的,“航天育种属于诱变育种,也就是利用辐射随机打断植物的基因,就像一个石头砸到一个基因上去一样,砸断以后如果碰巧产生好的变异,那就留下用,而基因编辑育种可以精准、高效地产生我们需要的遗传变异,也不留下外源基因。”
截至目前,CRISPR/Cas基因编辑技术在作物育种上已掀起了研究浪潮,并在提高产量、改善品质、提高除草剂抗性、非生物胁迫抗性、抗病性等方面都看到了巨大的应用潜力。
朱健康举例提到,其团队此前即利用基因编辑技术,通过调控油脂的代谢通路,阻断了油酸向亚油酸的转化,从而获得了油酸含量最高可达85%的高油酸大豆。“普通的食用油炸个五六次就已经不太好了,油脂中不稳定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就会转化为反式脂肪酸,对人体健康有影响,但高油酸油具有很好的热稳定性。”值得一提的是,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病不断增加的因素之一,就是摄入了过多的反式脂肪酸,在体内转化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这一高油酸大豆也是其团队目前申请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的品种之一。而在美国、日本等部分国家,基因编辑产品也已经先行一步正式走上了商业化之路。
以日本为例,2021年底,日本批准了GABA (γ-氨基丁酸)含量增加的基因编辑番茄用于商业销售,这也是日本市场上首个正式销售的基因编辑食品。GABA是一种天然存在的非蛋白质氨基酸,是哺乳动物中枢神经系统中重要的抑制性神经传递物质,具有稳定情绪、帮助降低血压等功效。日本筑波大学研究团队耗时15年时间,让这款西红柿的GABA含量比普通西红柿多4-5倍。
“所有的性状都是基因控制的,理论上来说都可以用基因编辑去进行改造。”朱健康强调,以提高产量为例,“它往往不是一个基因决定的,如果通过航天育种或者其他办法去支持,碰到一个基因不容易,两个基因同时碰到,这种概率基本是不存在的。但是现在基因编辑技术可以同时编辑2个基因、3个基因、10个基因甚至更多,能做的事太多了,以前想都不敢想。”
科研高产的另一面:国内需要打磨自己的“剪刀”
中国的基因编辑研究发展很快,论文与专利的数量均居于国际前茅,这是有目共睹的。
“就植物基因编辑这个领域,我们的研究人员群体比任何国家都大,国家也很支持,给予了很多资金上面的支持,做得也是比较早的,尤其是CRISPR/Cas技术出来后,国内的研究团队很快就用上了,所以从研究层面上来说,水平是处于国际领先。”朱健康总结道。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基因编辑不仅存在原始创新缺位的尴尬,在“产学研用”等各个环节也均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始创新成果。业内有专家曾写到:从最上游的基因编辑关键技术上看,我国的原创性技术和相关专利都远少于美国,现有基因编辑技术的核心专利基本为外国所有。从下游的基于基因编辑技术的农业育种、医疗方法及产品研发上看,我国在核心产品创新上也落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
上述情况非常不利于我国把握这一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朱健康也强调,“这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问题,就是这把‘剪刀’是别人的,用别人的‘剪刀’发论文没有太大关系,但你用这把‘剪刀’做出一个产品要去商业化,那是不允许的。”
在朱健康看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认为,目前在政策层面,国家已经非常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将基因与生物技术列为科技前沿领域攻关。
朱健康同样认为,自主创新“剪刀”的问题也有解决之道。“现在有两把‘剪刀’是用得最多的,一个是Cas9,另一个就是Cas12a,特别是Cas9效率也特别好,因为大家都用,一遍又一遍地去打磨。但是‘剪刀’在自然界里面其实很多,各种新的剪刀还是蛮多的。”
他认为,国内科研人员需要做的是,“要真正知道哪些是绕不过别人的专利保护,哪些是能绕过的并挖掘出来,我们要做这方面的尝试。”朱健康表示,“平时做做研究发发论文,用别人的‘剪刀’当然很轻松,但真要进行产业化,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剪刀’,这就好比医生需要有行医资格,是欺骗不得的。”
为了从已有的专利保护圈中杀出重围,朱健康及其团队对于新型Cas酶的开发做了大量的工作。据介绍,其团队涉及到Cas12家族的Cas酶的几项专利在国内已获得专利授权。他强调,与现有的CRISPR/Cas9基因编辑体系相比,这些Cas酶在实际应用时不会侵犯与CRISPR/Cas9有关的专利的权利。
“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就有意识开始布局这件事,经过这几年的改造,这些‘剪刀’进步特别快,可以说有些已经能媲美目前最好用的‘剪刀’了。”朱健康表示,“这些专利掌握在我们团队手中,在中国已经授权,在国外还需要一段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在朱健康看来,尽管大家都在强调产业转化的重要性,然而真正投入到这件事情上的人力物力并不多。“大家往往还是奔着论文去,但‘打磨剪刀’这样的工作并不会帮助你发影响因子很高的论文,因为从科学上来讲,这项工作的创新性并没有那么高,其实大家做的就是一件事,绕过别人的专利保护。”
朱健康表示,值得欣慰的是,其团队布局相对较早,大家也能形成共识去做这件事,“不是奔着论文去的,就是奔着解决‘卡脖子’的问题。”
此外,从技术层面上来说,朱健康认为植物基因编辑仍有提高的空间,“这个空间是持续存在的,但目前的技术已经足够支撑一些产业应用,这两者并不矛盾。”其提到的问题包括精准编辑、递送系统,以及基因和功能之间的关系等。
以递送系统为例,“‘剪刀’再好,但不能进到植物生殖细胞里去,这也就凸显了递送系统目前也是一个很大的限制。”朱健康提到,在自然界数十万种高等植物中,仅有远远不到0.1%的物种能够用现有的基因递送技术进行遗传转化和遗传修饰,“剩下的超过99.9%的植物,你想要做基因编辑是一点门都没有,无论什么样的工具都进不去。”
2021年10月,朱健康团队在The innovation期刊在线发表了题为“Cut-dip-budding delivery system enables genetic modifications in plants without tissue culture”的研究论文。他们指出,传统的方法如利用农杆菌或基因枪将遗传修饰工具递送进入植物细胞后,经过一个复杂的组织培养过程产生遗传改良植株,但是这个过程周期长,操作繁琐,并且大多数植物难以通过这一方法实现遗传改良。在近几年,虽然通过利用BBM、WUS、WOX5或GIF-GRF等植物再生基因或者利用病毒载体递送系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辅助遗传修饰工具的递送,但这些方法仍然有很大的不足,难以用在很多植物上。
研究团队则开创性地提出了CDB(Cut-dip-budding)递送系统。该递送方法操作极其简单,并且完全不需要组织培养过程,不需要无菌条件,通过简单的植物切断(cut)-沾菌(dip)-长根后生牙(budding)操作。研究人员目前已在草本植物(橡胶草、小冠花)、块根植物(甘薯)、以及木本植物(椿树、楤木、臭茉莉)中实现了转基因或基因编辑工具的递送。
“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中,递送一直是一个瓶颈。”朱健康谈到,科学界之前对这方面的关注度仍然不足,“最近开始关注的人多了一点,但还存在以发文章为导向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开发出更优的递送系统,能够用到大多数植物上,但现在的技术还做不到这一点。”
基因编辑育种商业化提速?先铺好“正道”
值得关注的是,去年的1月24日,农业农村部对外公布了酝酿已久的《农业用基因编辑植物安全评价指南(试行)》(下称“《指南》”),对农业基因编辑植物的安全评价管理进行了规范。
这次《指南》的出台被业内视为打破了之前我国基因编辑技术“研究领先、管理滞后、应用空白”的局面。然而,该《指南》的出台,是否就意味着国内基因编辑育种技术将加速走向产业化快车道?朱健康对此并不是全然乐观。
“这些年我花了不少时间去推动政策的出台,1月份的政策出台是好事,但我仍然希望这是一个过渡政策。”朱健康表示,尽管目前将没有引入外源基因的基因编辑植物区别对待,但现在的政策整体还是在转基因的框架下。“但无论如何,这个政策让我们看到了产业化的可能,但的确这条路要走完是比较长的。”
朱健康认为,对基因编辑育种来说,最优的政策显然是“一个更科学的态度”。他提到,无论是美国、加拿大、阿根廷等国家,还是传统上对转基因持反对态度的日本、俄罗斯等国家,“都出台了政策,把不引入任何外源遗传物质的基因编辑产品等同于传统育种产品,不按转基因对待,免监管的。”
实际上,在作物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实践中采取怎样的监管手段,各国政府尚未达成一致。有文献综述提到,概括而言,目前监管模式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以美国和阿根廷为代表的宽松型监管模式,这种模式以产品监管为导向,将基因编辑作物不视同转基因作物,免于严格的转基因监管;二是以欧盟大部分国家为代表的谨慎型模式,这种模式以过程监管为导向,把基因编辑作物等同于转基因作物进行监管;三是以澳大利亚等为代表的折中型模式,采用这种模式的国家在基因编辑作物的监管过程中,根据经济和技术发展阶段来调整相应监管法规和技术措施。
朱健康提醒道,从长远来看,如果监管不够科学,对产业会起到反作用,“可能很多人都不去申报了,更有一些团队会出现造假混用的恶劣现象;而对踏踏实实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发的团队来说,他们做的东西反而没受到保护,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此外,朱健康还强调一点,基因编辑育种产业化的成功必须依靠企业。“企业主体要把技术用好了,技术又要跟资本市场结合好,这才是正道。”他补充道,“资本市场真金白银支持,他要看的就是企业团队是不是有真正好的技术,能否做出真正好的产品。技术和资本之间的结合做好了,同时政策和创新保护也能做好,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领域才能够真正做大做强。”
然而,目前的现实情况则是,中国有几千家种子公司,但绝大多数并没有任何研发实力。同时,创新公司的前景也并不明朗。“资本其实找我们的很多,最热的时候每个星期都有几波人来谈。但最终大家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如果没有足够好的政策支持真正产业化,那我们的产品不能够走向市场,资本也不敢投很多钱进来。同样,如果创新保护做得不好,投的钱可能最后也打了水漂。”
朱健康再次谈道,从基础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国基因编辑领域的水平无疑已经处于国际先进,“但政策长期不放开,保护的问题也解决不了,最后产业就无法发展,从事这一领域的这么大的群体最后也是不可持续,连学生最后都找不到工作。”
他强调称,“产业不上去,光是自己在那发文章‘自娱自乐’,维持一阵子可以,但你不可能永远这样下去。”
声明: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均为采集网络资源。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







![基因测序行业深度研究报告:未来大健康领域黄金赛道[共77页] 基因测序行业深度研究报告:未来大健康领域黄金赛道[共77页]](/static/upload/other/20230126/1674744324488315.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