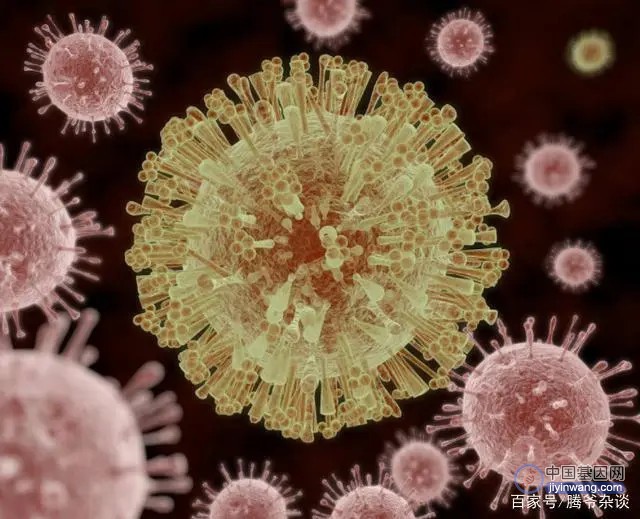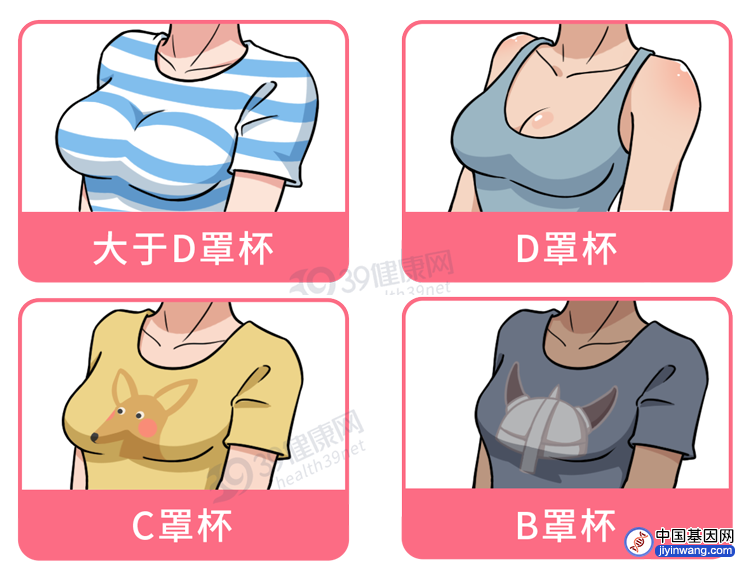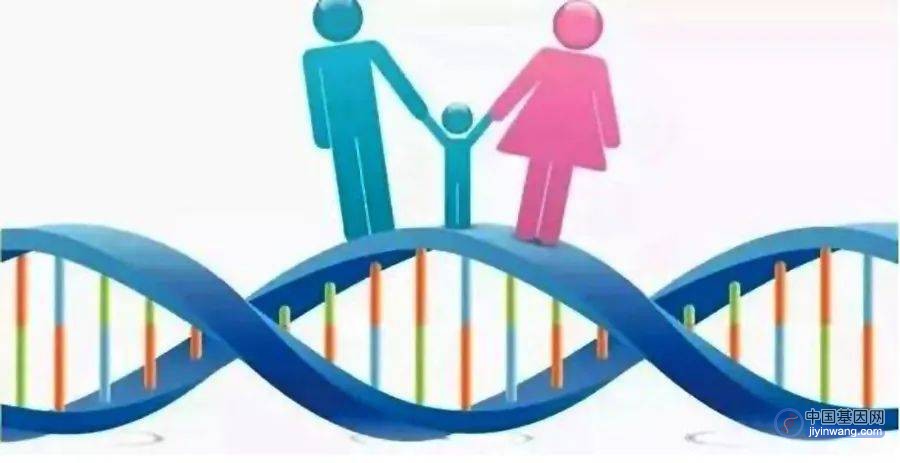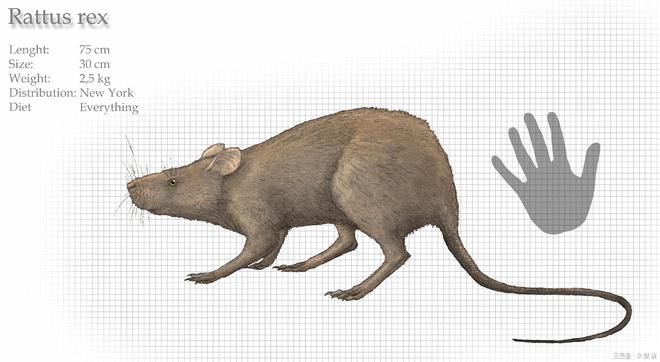《物种再起源》:将已灭绝的动物带回人间

猛犸象
制造恐龙比你想象的要难。在《侏罗纪公园》里,人类从保存在琥珀里的蚊子身上提取了完整的恐龙DNA,然后将其克隆了出来。但是DNA会随着时间降解,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在史前的蚊子或恐龙化石中找到任何DNA。更现实的方法是从身边已有的活恐龙下手:鸟。现代鸟类被认为是兽脚类(theropod)恐龙中幸存下来的一个分支,与霸王龙和迅猛龙关系密切。(只需看看它们的爪子:“theropod”的意思是“长着兽类的脚”)通过干预鸟胚胎的发育方式,你可以让某些现代的适应基因失效,让旧的基因指令起作用。雄心勃勃的研究人员已经创造了一只有长着鼻嘴而不是喙的鸡。
很显然,这会增加世界的总体欢乐,最终将推动类似侏罗纪动物的宠物贸易蓬勃发展。然而,居然有很多其他项目想要复活消失不久的野生动物,比如长毛猛犸象或者比利牛斯山野山羊。基因编辑技术的进步有望使“灭绝动物恢复”成为一项可行的事业,但是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瑞典科学记者托瑞尔·科恩菲尔德(Torill Kornfeldt)采访了多位研究人员,写成了《物种再起源》(Re-Origin of Species)一书。这本书表面看起来流畅易读,却提出了许多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层问题和悖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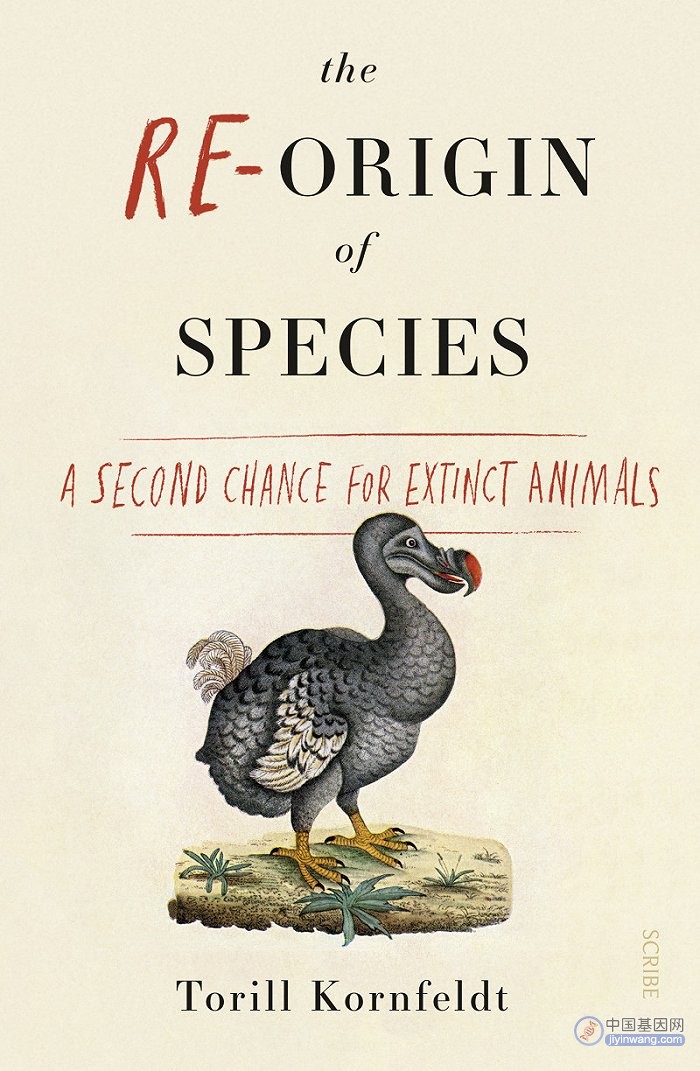
《物种再起源》
最后一只猛犸象的死亡时间不过4000年,这意味着人们可以复原猛犸象DNA的片段,而科学家们已经拼凑出了猛犸象基因组与现代大象基因组的所有不同之处。在西伯利亚,特立独行的猛犸象骨骼猎人谢尔盖·齐莫夫(Sergey Zimov)希望将猛犸象重新引入这片土地,而美国遗传学教授乔治·丘奇(George Church)正在研究将猛犸象序列拼接到大象DNA中的方法,以便创造猛犸象。但是为了什么呢?丘奇的动机很简单:在进化的过程中创造新的甚至是改进性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种乐趣。(“我们甚至可能比猛犸做得更好,”他说。)齐莫夫和他的儿子指出,如猛犸象之类的巨兽,因为它们会破坏吸收热量的森林里的树木,翻开土地上隔热的雪层,所以实际上可以保持环境整体温度下降,从而减缓全球变暖。
当然,这只有达到一定规模之后才会起效:如果有数百万猛犸象和庞大的原牛群(现代牛的野生祖先),以及其他过去的幽灵物种在欧洲大陆漫游的话。这样的世界确实是一些人想要看到的。在一点上,“灭绝动物恢复”的想法与现代“重新野化”运动的愿望相契合,后者希望通过重新引入包括狼这样的食肉动物在内的野生动物,改变发达世界的生态系统。
这样做法的部分动机仅仅是审美,还有一部分来源于我们这个物种的负罪感。到底是人类还是早期的气候变化杀死了猛犸象、大树懒和其他大型动物,科学家尚未取得共识,但是在一些人看来,恢复这些物种将是对我们所有其他环境破坏行为的一种象征性补偿,让我们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回到人类堕落前的那种纯真状态。高科技生态学的反文化教父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告诉柯恩菲尔德:“例如,我希望海洋中的鳕鱼和以前一样大。人们去非洲的国家公园,能看到热带草原上全是动物,丰富多样,数量巨大。欧洲曾经是这样,北美曾经是这样,甚至连北极也有着如此丰富的动物群。这是我的目标。"

已灭绝的大地懒
照这样的观点来看,比起令人激动的环境变化——布兰德用“生物丰富”来形容这种环境——来说,猛犸象或狼、更不用说凶猛的恐龙造成的一点人类死亡是可以接受的代价。(瑞典的野猪是20世纪80年代从公园逃出来的几只野猪的后代,现在每年都会造成成千上万起交通事故。)事实上,还有一名研究人员正致力于将旅鸽带回美国——数百万只旅鸽会定期摧毁美国当地的植物群——研究者认为这正是旅鸽需要扮演的创造性破坏角色。(“森林不时需要森林火灾,”他说。)这种愿景显然来自于生态的怀旧,一种恢复原状并保持原样不变的愿望。由此产生了一些项目,比如在新西兰沿海岛屿上消灭“入侵的老鼠”,这只不过是一种生态上的优生学。
但是,该领域的其他思想家也早就注意到,任何生态系统本身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正如柯恩菲尔德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当下的自然比1万年前的自然,或1万年以后还会存在的物种更有价值?”荷兰生物学家门诺·席尔图岑(Menno Schilthuizen)最近出版的《达尔文驾到》(Darwin Comes to Town)一书,正是对这种想要逆转地球时钟的生态学的绝佳反驳。该书调查了加速进化是如何驱使各种动物在我们的城市中找到新的生态定位的,并展示出了极大的欣慰和乐观。
另一种对“灭绝动物恢复”的批评更加实际,即认为它分走了拯救尚未灭绝的物种所需的资源。但是这两件事并不一定是非此即彼的:拿世界上仅有的两只幸存的北白犀牛而言,它们可能是互补的。柯恩菲尔德参观了圣迭戈的冷藏动物园,该动物园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收集了近1000种冷冻在液氮中的物种细胞。通过克隆12头犀牛的细胞,动物园园长奥利弗·赖德(Oliver Ryder)希望可以重建可持续的北白犀牛数量;或者,用柯恩菲尔德的妙语来讲:“12个试管可以让新生犀牛再次像微型装甲车一样横冲直撞。"
冷藏动物园还保存着已经灭绝的一些物种的细胞,例如夏威夷毛岛蜜雀,那是“一种眼睛周围戴着黑色面具的灰色小鸟”。当科学家们争论是否要去捕捉幸存的鸟时,它们的数量在持续减少。最终,一只雄性被抓住了,但是没能找到一起繁殖的雌鸟,而它也在2004年死亡了。它的细胞被送到了赖德那里,“那是圣诞节前后,”他告诉柯恩菲尔德,“当我坐在显微镜前检查细胞时,这种感觉戳中了我——这个物种已经消失了,那是一种尖锐而强烈的意识。”
在这个领域,没有正确或错误的答案,但是正如柯恩菲尔德暗示的那样,这种辩论的言辞仍然围绕着一些甚少被深入探究的假定美德。例如,她采访的一些“灭绝动物恢复”计划的研究人员,常常援引更大的“生物多样性”目标,实际上它们从来都不是绝对的目标。如果我们消灭携带疟疾的蚊子——也许正如研究人员现在试图做的那样,用基因不育的蚊子来代替它们——我们每年可以拯救数百万人的生命,但这无疑将减少生物多样性。某些真菌能让人类最喜爱的某些树种陷入灭绝险境,但它们本身也是有机体,就像它们攻击的树木一样。不可避免的是,讨论这些理念的人总是选择一个物种,而放弃另一个物种,并且认定某种生态系统比另一种更加本真——然而,自然本身并不在乎孰优孰劣,毕竟它是地球上最残酷的灭绝机器。
声明: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均为采集网络资源。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